元代织物中鹿纹研究
- Update:2014-04-27
- 刘珂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3期
内容摘要
元代织物中鹿纹形象占有一定数量,织物中的鹿纹目前主要归于“春水秋山”题材,在辽、金织物及元代青花瓷中亦有大量鹿纹形象。鹿纹形象流传历史久、范围广,文化内涵丰富,文章主要通过鹿纹的相互比较,归纳造型特征及文化背景。
《蒙古秘史》中蒙古人“苍狼白鹿”的图腾传说,加上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对鹿的熟悉,不难理解为何元织物中有鹿纹形象占有一定数量,并且在辽、金时期的织物中鹿纹形象也常常出现,专家常将鹿纹称作“秋山”,成为独具游牧民族特征的纹样。其流行的时间久远,早可追溯到“斯基泰”文明。同时鹿在汉文化中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是贵族及百姓喜闻乐见的祥瑞。早在史前岩画上已出现鹿纹,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也有鹿纹形象,商代鹿纹玉雕已可见神形兼具的鹿纹,周代鹿与龙、凤、龟共为四灵之一的麒麟,唐朝时期的玉雕鹿纹已开始强化鹿纹的吉祥寓意,口吐灵芝云气,由早期站立姿态转为卧姿为主,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鹿与“禄”、“六”谐音,虽然鹿形象代表的含义有所区别,但吉祥寓意一直保留为人们所喜爱。下面将元代织物中的鹿纹形象与同时期的金银器、绘画、玉器、青花瓷以及与辽代织物中的鹿纹形象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归纳元代织物鹿纹造型特征。
一、元代织物中的鹿纹

1. 鹿纹织金金绢
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出土。滴珠窠内饰一卧鹿,巨大的双鹿角,身边漂浮小朵云。(图1)

2. 鹿纹方补织金绫片金
香港万玉堂藏。方形补子内装饰一站鹿,四周装饰花草、祥云,总尺寸105×100 厘米,方补尺寸29×30.9 厘米。(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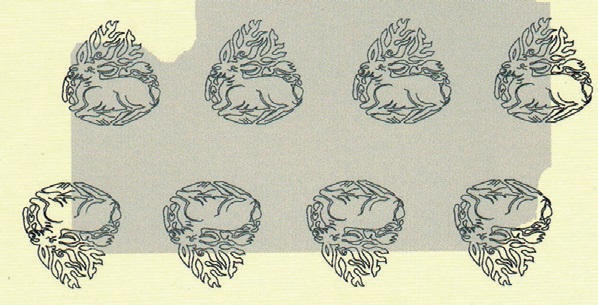
3. 紫地卧鹿纹状金绢
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图案构成为滴珠散搭形式,主题图案为一头戴珊瑚双角的卧鹿,空隙处隐约有树叶纹填空。组织为平纹地上1/5S 斜纹妆花方式织入片金,反面每隔16、20 或29 纬不等处出现地纬的背浮,每次背浮为6 根纬线。(图3)

4. 紫罗地花鸟纹刺绣夹衫
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出土,藏于内蒙古博物馆。松树脚下一灵芝,旁边一鹿头顶灵芝鹿角,疾奔回首,这是传统的汉文化吉祥图案。(图4)
二、分类
总结元代织物中的鹿纹题材,可分以下四类:



1. 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图案是金、辽人服饰常用题材,春水多指鹘捕雁鹅,秋山多指鹿纹及山林景象。辽、元织物中鹿形象也有山间飞奔,被海东青捕猎的景象,这类鹿图案造型较为写实,鹿多以飞奔的运动姿态,有侧面和正侧面角度,画面生动自然。例如罗地压金彩绣山林双鹿、罗地压金彩绣团窠飞鹰逐鹿。(图5、6,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墓出土,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
比较发现,表现狩猎的“秋山”鹿纹题材在辽的织物中有明确展现。契丹族在《辽史•营卫志》中载,契丹族“随水草就略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即集而射之。”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从文献记载也可感受围猎时呼鹿呦呦,鹿惊飞奔的激烈场景,能展现此场景的画面也必定是动态的。
2. 源自中亚西亚鹿纹形象
珊瑚状大角鹿在元织物中特征明显,鹿体型健硕,夸张的珊瑚状鹿角凸显鹿气宇轩昂,姿态以昂首站立或俯卧的静态为主。在鹿周边空隙处以花草或云气纹填补,画面图案装饰性强,完全以图案组织画面适合于滴珠窠或方形内。此类图案化造形鹿,专家一般也划归为“秋山”题材。然而鹿作为草原艺术独特的装饰纹样已具有悠久历史,斯基泰艺术专家研究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 世纪至前3 世纪,在已发现的文物中即有夸张的鹿相互撕咬,波浪形鹿角特征明显,以及散落在蒙古草原上带有波形鹿角的鹿石都展现了西亚、中亚早期文明对鹿形象崇拜的悠久历史。[1] 早到距今两三千年左右在藏西和藏北高原地区的岩画中,鹰和鹿的表现形式是动物形象中最早具有装饰化和图案化特征的,说明鹰和鹿在高原先民的意识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含义。并且西藏早期宗教或神灵崇拜意识密切相关的形象,说明鹿纹在高原、草原文化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银盘鹿纹图案与元织物图案造型极为相似,圆盘中心一头戴灵芝角的立鹿,神情安详地注视远方,周围衬以果叶形成适合圆形。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初期大量联珠鹿纹锦中,其形象一律为大角鹿形象,并且在萨珊及之后七八世纪的粟特工艺品装饰上也较为常见,这种体型壮硕无比的鹿是来自西亚的马鹿,鹿角多达8 叉。出土的织锦中鹿主要为三种组合造型:在联珠纹中装饰单只站立缓步前行的鹿,或两只相对站立的鹿,或在中心花树下边分别站立的一对鹿。收藏于比利时辉伊大教堂带有粟特文赞坦尼奇(Zandaniji)字样的织锦,专家将此件织物定为中亚所产的粟特锦,中间也是对鹿图案。唐织锦也常用这三种组合形式装饰羊、马、牛等动物,表明这种以站立姿势并图案化处理表现动物的造型特征已非常成熟,动物形象及周边填空图形组合以适合于圆形联珠纹。唐织锦中鹿常佩戴绶带,端庄稳健的造型感受到人们将鹿视为祥瑞而崇拜敬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 记载:突厥祖先是海神射摩舍利,与以鹿为图腾部落的海神女结缘,在一次大猎中射摩舍利没有射中出现的金角鹿而与海神女断了情缘。《蒙古秘史》开篇记载蒙古族“苍狼白鹿”传说,鹿为母系之始祖,狼为父系之始祖,蒙古族将鹿视作祖先,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传说都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置于母系位置,间接说明了公元前两千纪中叶至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以前在欧亚草原和蒙古高原西部称雄的以鹿为图腾的文化,在突厥汉国兴起前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因此,元朝贵族喜用鹿的图案就不难理解,但是元代织锦中以站、卧姿势出现于滴珠窠或方形补的图案化鹿纹形象应区别于奔驰在山间、田野的写实动态的鹿纹“秋山”题材,织锦中出现的这类鹿形是源于中亚、西亚及草原文化对鹿的图腾崇拜,画面传递的信息不是猎捕鹿而是敬仰鹿。
3. 源自汉民族吉祥寓意
织物中除了展现草原文化的鹿文化,还展示了中原文化中鹿所代表吉祥寓意的汉文化特征。私人收藏的压金彩绣松鹤鹿纹枕套,灵芝、鹿、松鹤、鸳鸯及祥云、花草,纹样以刺绣技法表现较为写实的动物造型,祈求带来如意、长寿、夫妻恩爱等美好愿望,只是图案组合明显还未形成固定的组合模式。早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鹿角立鹤”铜鼓,表明在汉文化中已将夸张的鹿角并与鹤结合成想象的神兽。商、周、战国时期的玉鹿、银鹿的形态中夸张的大鹿角造型或卧、或立回首的动态都已确定了造型雏形。汉代鹿已被认为是祥瑞,汉代郑众《婚物赞》说:“鹿者,禄也。”《淮南子》云,“鹿鸣兴于兽而君子美”。鹿与柏树组合意为“百禄”,与桐树组合意为“同春”。《述异记》云:“鹿千年化为苍。又五百年化为白。”表明鹿是长寿的象征。汉代常出现的祥瑞麒麟也是以带翼鹿形象出现,麒麟两字都有“鹿”字偏旁,是以鹿类动物为依托的有翼神兽。唐代织物上出现的佩戴绶带的鹿也表明其祥瑞的身份。金、宋代玉雕配饰中也有鹿、灵芝、竹子、天鹅的纹样。至元代鹿逐渐被赋予多种吉祥的寓意并开始与其他吉祥图形组合出现。在元代玉雕作品中,出现双鹿头顶灵芝祥云立于福字团窠中,显示出汉文化中追求吉祥寓意的愿望,在游牧民族中一样得到共鸣。因此元代织物中的鹿纹也不能一概论为是源于游牧文化的“春水秋山”,是元民族的图腾崇拜,还是中原文化对吉祥寓意的追求。可见,明清流行的“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吉祥图案,在宋、金、元代已出现流行端倪,开始将有吉祥含义的动植物有意识地组合运用,但画面组合还不够精炼成熟。明清时期吉祥图案画面更加简洁,其他仅填补空隙无吉祥寓意的花草一概省略,利用谐音等逐渐将动植物组合形成固定模式,代表确定的吉祥寓意,并做到每幅画面“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图7,银祥瑞图帔坠,湖南临灃新合窖藏出土)
4. 鹿纹在不同宗教中所代表的寓意
鹿在不同宗教中所代表的寓意也不同,佛教中鹿是唯一能够确定灵芝位置的神兽,鹿角尖部含有灵芝的精华。[2]汉朝起就普遍迷信世上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灵芝仙药,笃信人能长生不老的道家对它更是百般寻觅。在藏族艺术中鹿常为雌雄成双成对出现,代表着和谐、幸福和忠诚。牡鹿是美索不达米亚天神安努的一种化身,象征凯尔特的男神塞如诺斯。塞如诺斯是猎人的吉祥神,被认为是百鹿之王,通常以长着鹿角或角的拟人化形象出现。在希腊罗马神话和艺术品中,牡鹿是司狩猎的女神阿尔忒弥斯/ 狄安娜的象征。在文艺复兴寓言中,牡鹿是听觉感官的标志,谨慎德行的标志。
结语
元代织物中出现较多鹿纹形象其文化影响渊源多元化,除了受游牧民族“春水秋山”题材影响,还有来自中亚、西亚对鹿的形象崇拜,也有中原汉文化视鹿为祥瑞表现吉祥寓意因素的影响。宋元时期“秋山”题材已与汉文化相互交融,鹿与其他吉祥植物组合表现吉祥寓意,初显明清时期成熟流行的吉祥图案之端倪。织物中鹿纹呈现或卧或立的静态姿态,是受中亚、西亚对鹿的崇拜影响。鹿呈现飞鹰逐鹿的动态形势,才是源自北方游牧民族“春水秋山”题材,不能简单将元织物中所有鹿纹统归为“秋山”。
注释:
[1]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5,第14 页。
[2](美)詹姆斯•霍尔、克里斯•普利斯顿:《东西方图形艺术象征词典》,韩巍、徐延波、郝一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0。
参考文献:
[1] 赵丰:《中国丝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2] 尚刚:“吸收与改造——6至8 世纪的中国联珠圈纹织物”,赵丰等主编:《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 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5。
[4] 杨伯达:“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