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阿瑟·丹托的《寻常事物的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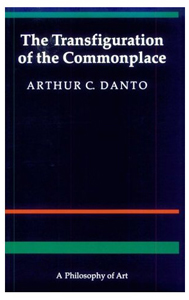
阿瑟•丹托(Arthur Coleman Danto)生于1924年,是美国、乃至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美学家。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雷尔•卡罗(Noël Carroll)曾中肯地评价说,“阿瑟•丹托有关艺术哲学的著作,在20世纪后半叶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1995年)。时至今日,丹托仍然是国际艺评界和美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针对丹托的美学思想,迄今已举办过三次较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是2006至2007年间关于《寻常事物的变形》一书的网络研讨。
丹托的《寻常事物的变形》一书写于1970年代中后期,发表于1981年,是对其早期论文《艺术世界》的进一步扩充和展开。1964年11月,安迪•沃霍尔在纽约举办了首次个展,受此启发,丹托在这一年岁末的哲学年会上提交了《艺术世界》一文。据其弟子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回忆,沃霍尔的纽约个展对于丹托而言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在1950年代,丹托已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从事表现主义木刻的创作。与此同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是选择做职业艺术家还是哲学教授?看过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后,丹托决定放弃艺术,全身心投入哲学。
从1964年到1981年,丹托在哲学界获得了巨大成功,不过,他的《艺术世界》一文起初并不为人注意,他的工作重心也不在艺术哲学方面。《艺术世界》在1970年代引起较广泛的关注,托赖于另一位美国哲学家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迪基小丹托两岁,受丹托论文的启发,他就如何定义艺术提出了“艺术惯例论”(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这种理论认为,某物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是因为艺术界人士授予它以鉴赏的资格。不幸的是,丹托认为,这一理论严重误解和歪曲了他本人的思想。与此同时,丹托对当时流行的维特根斯坦主义也感到不满,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论点是,我们既不能定义艺术,也不需要定义艺术,而丹托却持相反的观点。诸多原因促使他重新返回艺术哲学,对艺术的定义或者说艺术的本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1984年,丹托应《国家》之邀,继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劳伦斯•阿洛韦之后,成为该刊的特约艺术评论员。丹托以批评家的身份积累起来的声名,极大地促进了其哲学思想的推广,使他成为继格林伯格和斯坦伯格之后在美国影响最大的艺术理论家。
 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对于丹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哲学问题:两件从外观上无法分辨的东西,为何其中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出发,丹托展开了他别具一格的美学思考。前卫艺术家们用“现成品”来取消艺术品与寻常物品的界限,迪基的“艺术惯例论”从外部来定义艺术,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如莫里斯•魏茨(Morris Weitz)和肯尼克(William Kennick)等人则主张艺术不可定义,但这些都不是丹托所期待的答案。
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对于丹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哲学问题:两件从外观上无法分辨的东西,为何其中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出发,丹托展开了他别具一格的美学思考。前卫艺术家们用“现成品”来取消艺术品与寻常物品的界限,迪基的“艺术惯例论”从外部来定义艺术,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如莫里斯•魏茨(Morris Weitz)和肯尼克(William Kennick)等人则主张艺术不可定义,但这些都不是丹托所期待的答案。
在《艺术世界》中,丹托用“风格矩阵”演绎了艺术史的演变,每增加一种新的艺术定义或者说艺术理论(例如,艺术是再现的,艺术是表现的),就会增加(2n+1-2n)种可能的艺术风格。什么是艺术?艺术是由艺术理论的排列组合所构成的可能世界,在由此构成的风格矩阵中,现实的艺术风格或艺术作品不过是矩阵中的一行,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组合。与一般的可能世界理论不同,丹托的可能世界是历史性的。布里洛包装盒与以往艺术品的不同,在于它否定了以往所有的艺术定义。标准的艺术定义方式是,艺术品是具有某特性的某物。如,艺术品是具有{a, b,…n}特性的某物。然而,布里洛包装盒就是布里洛包装盒,是负{a, b,…n},是对以往全部特性集合的否定,就此而言,即便在艺术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艺术定义,比如n+1,布里洛包装盒也仍然会对它进行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布里洛包装盒实际上并不是矩阵中的一个元素,而是对整个矩阵的否定,而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否定,是因为艺术世界的诸种排列组合已渐次展开,艺术世界作为一种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已经昭然若揭。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等现成品蓄意揭示了艺术世界的整体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演进为有关艺术的自我意识,也即艺术哲学。后来,在《寻常事物的变形》一书中,丹托将艺术演进为哲学称之为艺术史的终结。
《寻常事物的变形》延续了《艺术世界》中对可能世界及艺术史终结的基本思考,却没有保持《艺术世界》中相对单一的线索。《寻常事物的变形》是一部相当晦涩的著作,与其说它进一步阐发了《艺术世界》中的结论,不如说它让原本相对清晰的结论又退回到思想的半途中,在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思想岔道上逡巡徘徊。.jpg)
两件看似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何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则不是?在《艺术世界》中,Testadura,一个虚构出来的俗人的代表,认为布里洛包装盒就是布里洛包装盒,而不是别的什么。在《寻常事物的变形》中,一位从事艺术的愤青,“J.Seething”先生,愤然质问,凭什么杜尚拿来的小便池是艺术品,他拿来的小便池就不是?通过T先生,丹托想问为什么布里洛包装盒或杜尚的小便池是艺术品,而其寻常世界的副本却不是;通过J先生,丹托追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杜尚的小便池之后,艺术与实物究竟有何区别,艺术是否仍然有其边界。
对于前一个问题,《寻常事物的变形》提供了更为精细曲折的论证,甚至达到了不惜笔墨的程度,但最终交给读者的答案却相对来说较为简单。这个答案是:艺术品与其寻常世界中的副本的区别,并不在于物理属性,而在于它们各自所处的关系。为了澄清这一问题,丹托列举了各式各样的例子,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营造理想的哲学情境而虚构出来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曾引发现实中的艺术家效仿和热议的“红方块系列”。丹托构想了这样一个展览,有九幅尺寸质地相同的画布,涂满了相同的红颜料,第一幅是克尔凯郭尔描述过的一幅画,题目是“以色列人穿越红海”;第二幅是由一位心理洞察力极强的丹麦肖像画家创作的作品,名字叫“克尔凯郭尔的情绪”;第三幅题名为“红场”,机智地表现了莫斯科的风光;第四幅是极简主义绘画,碰巧的是,它的标题也叫做“红场”;第五幅是宗教绘画,题名为“涅槃”;第六幅是由马蒂斯的门徒捉笔的静物画,叫做“红桌布”;第七幅是来自乔尔乔内作坊的敷了底色的画布;第八幅是用铅红上色而不是敷了底色的画布;第九幅是艺术愤青J先生拿来参加展览的题名为“无题”的作品。前六幅显然都是艺术品,而且属于不同的类别:历史画,心理肖像画,风景画,几何抽象画,宗教画和静物画。第七、八幅显然都不是艺术品,前者由于乔尔乔内亲自敷了底色,虽然不是艺术品,却具有艺术史的价值,后者却是不折不扣的“纯然之物”(mere thing),无意于步入神圣的艺术殿堂。第九幅是件有争议的作品,丹托勉强算它是艺术品,却宣称它是“空洞”的。
从上述例子可知,无论是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区别,还是艺术品与艺术品之间的区别,都不必然在其可感知、可分辨的物理属性方面。上述九件展品共享了相同的“物质副本”,却分属不同的类别,即是一个明证。丹托认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之所以断言艺术不可定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因为他们假设艺术品所具有的属性都是物质性的,从千差万别的物质属性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属性,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如丹托所说,“假如我们将范围扩展到那些不可见的属性上,就可能会在迄今为止在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看来是异质的一类东西中发现一种令人惊讶的同质性”。丹托所说的为艺术品共享的“不可见的属性”,主要是指关系属性。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在于它和当时的艺术世界处在某种关系中,“我们可以设想,彼此毫无相似之处的东西,因为最后都满足了这一关系,便都成了艺术品”。为了说明什么是关系属性,丹托构想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孩,他的叔叔全都是中年白种人,但他的祖母现在决定嫁给一个中国人,她和这个中国人生了一个的孩子,现在把这个东方面孔的小婴儿送到那个小孩面前,告诉他这是他的叔叔,情况会怎么样?很显然,叔叔之为叔叔,不是由可见的属性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家族关系决定的。在丹托看来,“艺术品”和“叔叔”都是某种关系概念。
在丹托看来,使某物成为艺术品的“关系”,多半是历史性的。同样是一条被平涂成鲜蓝色的旧领带,如果出自晚年毕加索之手,便有可能是艺术品(可以设想,他试图用平涂的手法拒绝抽象表现主义对笔触的神化),而在塞尚那里,同样一条涂了颜料的领带却不可能成为艺术品,丹托在书中说,“我们甚至不清楚,塞尚是否会产生以这种方式制造艺术品的念头,因为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艺术概念”。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列举了很多,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通过这些半真半假的例子,丹托早年的思想在本书中得到了延续和扩展。
然而,对于上述通过J先生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如果布里洛包装盒或杜尚的小便池是艺术品,那么,凭什么J先生的“红方块”就不是艺术品?如果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那么艺术品和寻常之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丹托的一个试探性回答是,艺术的边界在于所有的艺术都是有所关于的,艺术品的“关于结构”(aboutness)使得艺术品和它难以分辨的物质副本有了区别。显然,这种“关于结构”并不是肉眼可观察的属性,而是依赖于“艺术世界/可能世界”的逻辑“关系”。丹托指出,杜尚或沃霍尔的作品所关于的,不是以往艺术所关系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内容,而恰好就是“关系结构”本身。艺术发展到这一步,就成为了关于艺术的哲学,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艺术史便走向了尽头。
在书的结尾部分,丹托如此评价布里洛包装盒进入艺术世界的意义:“这一寻常事物的变容,到头来并没有改变艺术世界中的任何东西。它仅仅是让人们意识到了艺术的结构,毫无疑问,在那一隐喻成为现实的可能之前,这一艺术结构尚需一定时间的历史发展。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类似布里洛包装盒这样的东西就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毫无意义的。其不可避免之处在于,不管是用它还是用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得不摆出某个姿态。其无意义的地方在于,一旦我们能造出这样的东西,也就没有理由再去制造同样的东西”。按照我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托在这部书的开头部分暗示说,艺术愤青J先生创作的“红方块”是空洞的。
丹托的文字是才子的文字,多数问题点到即止,很少做系统的总结,读者稍不留神便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我们需留神的是,丹托在回应第二个问题时所做的论证,与回应第一个问题时的论证是有所不同的,此外,“关于结构”也并不等于前面所提及的“关系概念”。依照我粗浅的理解,丹托的前一个论证涉及到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界限,后一个论证涉及到评判艺术品好坏(或有无意义)的标准。在回答后一个问题时,丹托依托于“关于结构”的论证,似乎是在强调和突出艺术品的内容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丹托似乎并没有比以往的美学家走得更远。在该书的最后两章第六章《艺术作品与单纯的再现》和第七章《隐喻,表现和风格》中,丹托似乎回到了传统美学对再现论和“形式/内容”关系的讨论。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品是具有一定内容的形式,丹托的特别之处,仅仅在于他认为作品的“内容”是可以随情境而改变的。如前所述,同样一张涂成红色的画布(丹托所说的“物质副本”,我们所说的“形式”),可以是历史画、心理肖像画、几何抽象画或者是观念艺术作品,也可以是一张简简单单的画布,是说不上有所关于、也说不上无所关于的“纯然之物”。依此推断,丹托最终的结论似乎可以概括为:凡是艺术品,都是对“内容”有所表现的,J先生的“红方块”尽管也有内容,但这内容却是空洞无意义的。(如果这就是丹托的底牌,那么是否暗示着,尽管丹托热心参与评说当代艺术,却对以布里洛包装盒为代表的当代艺术保持着一种貌似神离的距离?)
我曾花费数年光阴仔细研读和翻译丹托这部艰深难懂的著作,如果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望不到结论的终点,那么当我最终完成翻译并得出结论时,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把丹托理解得过于简单了。关于丹托这部书的讨论,犹如汗牛充栋,我的看法只会是以往诸多看法中的一种,然而我却希望通过这些不成熟但相对来说较为清晰的看法,激起更多读者阅读和思考丹托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