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年来中国木版画的全面梳理——张道一先生新著《中国木版画通鉴》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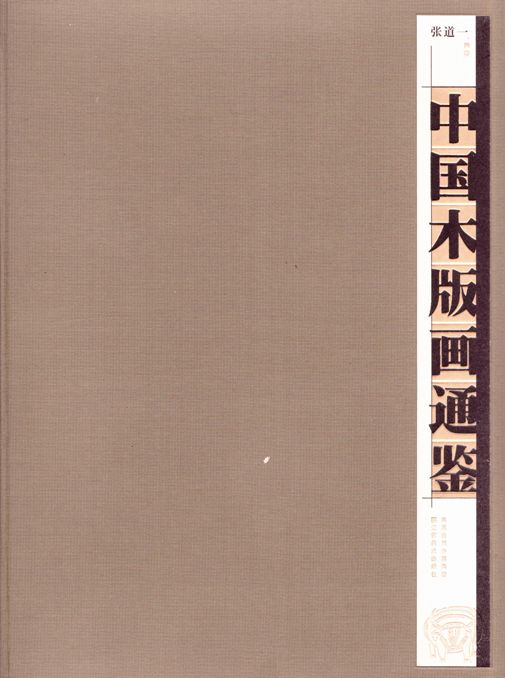
中国木版画传统渊源有自,在20世纪的美术史上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予以关注,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传统的木版画遭受到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冲击,在美术领域几乎构成了一个新的版画范畴。鲁迅先生因此在30年代提倡“新兴木刻运动”,在介绍西方版画作品时指出,这是“木刻回娘家”,表明中国才是世界木刻画的发源地。
对于如何整理和继承中国木版画传统,在50年代以来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南北两地学者的关注。1954年,阿英先生出版了《中国年画发展史略》;郑振铎先生在50年代初编成一部《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和一部《中国古木刻画史略》手稿,两部遗稿最终于1985年正式出版;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版画史》也在1961年问世。这几部著作是木版画研究中的重要之作。但阿英所作是一个年画的专题研究,王伯敏则以明代版画为重点,郑振铎本想对中国木版画进行整体研究,由于当时资料和认识有限,加上早逝,也未能有全面性地研究。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30年,虽有不少中国木版画研究著述出版,但大都仍是以类别或地域性的专题为主,全面整体地包罗皇家、官方、文人、商家、宗教和民间的木版画研究依然阙如。
张道一先生集几乎一生的收集研究,于78岁高龄撰成《中国木版画通鉴》一书,(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1月版,以下简称《通鉴》)是继此之后美术史研究的一部力作,《通鉴》分上下二卷,上卷为“历史长河——一千二百年”,下卷为“全面分类——一千二百例”。第一次全面刊布了1200年以来中国先民们所创造的120多种木版画,全书收图总计1317幅,包括大量散见或稀见的木版画种。本书以学术思想的独特和全面细致的编纂分类方式,对于中国木版画全方位观照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对于木版画概念范畴的辨析和重新阐述,以及“在一般中看出优异,在大众中托出精英”等精彩论述均为本书的亮点。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本《通鉴》是当前中国古代版画史研究水平的标志。
一 木版画概念的重新阐述
一般认为“木版画”一词是指一切“木版刷印画”;也有研究者将木版画分作年画和插图二大类,在年画类下收入纸马、纸牌、门笺等;还有一种所谓“以刀代笔”的说法,显然是与一般绘画混为一谈,没有看到木版画非凡的创造性。以上几种说法有的在概念上的模糊和逻辑上的混乱是因理解错误和先入为主的研究方式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方式是以最先获得的木版画直观印象或说法为主,对后来接触到的各种不同木版刷印画采取一概排斥态度。如果木版画仅年画和插图二类,那中国木版画创造成就就显得太可怜了,更不能显示出木版画“娘家”的富足了。将纸马之类当作年画在概念上也含糊不清,因为纸马并非年节张贴之物。
张先生从中国木版画的实际出发,厘清木版画的概念并作了重新阐述:“究竟什么算‘木版画’?我的理解是广义的,就是用木版印的图画。也就是说,一千二百年的刻版,除了刻字之外,凡是刻图的都属于‘木版画’,其范围无疑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大汇总,因为大,才体现出总。”(《通鉴》,604页)张先生也不赞同一切木版刷印画都是木版画的说法,因为印染方面的“木版印花”与“雕版隔染”即夹缬都不能属于木版画,它们只是对木版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样的概念梳理与分析阐述中,我们感到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继承与创新责任的自觉承担与自信。
二 全面、细致的编纂分类
和以往木版画研究不同,《通鉴》在编纂分类上最大的特点是全面细致,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虽曰分类,但在类的划分及种的归属上,却彰显出张先生对于庞杂繁多的中国木版画深刻的认识和学术思考。他说:“将我国的木版画作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使其纵横贯通,纵向发展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横向开拓分作十二大类,一百二十种,并列举一千二百个图例,以窥全豹,可谓壮观!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为了全面认识我们民族的过去和传统,将木版画看作一个整体,一个艺术门类,以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通鉴》,13页)这12大类120种主要是:(一)年画类,33种;(二)灯画类,3种;(三)幡画类,10种;(四)插图类,17种;(五)供奉类,16种;(六)符咒类,10种;(七)游艺类,7种;(八)玩具类,4种;(九)契证类,4种;(十)印记类,5种;(十一)扎糊类,7种;(十二)饰纸类,4种;另类,1种。这确实是一个“大汇总”与“大观照”,其中可见全面细致两个特点:
其一,《通鉴》不以官方刻、商家刻、民间刻等所谓高低雅俗为中心来限定取材范围,而是以功能划分,对那些不被关注的契证类、扎糊类、玩具类等与版刻刷印相关的各种木版画品种均作全面搜求、细致查考,再作综合归类排列。1200多幅作品既包括门神、中堂画、名人绣像、祖师图、叶子及宗教供奉用纸马、门笺、财神等我们较为熟悉的作品,也有标签、仿单、银票、婚书、护符、戳印、走马灯、鞭炮纸、戏衣绣稿、嘛呢旗、佛前挂钱和冥界文书等不为大家甚至研究者熟知的“资料”。选取之全,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个庞大刷印艺术群的中国木版画丰富多彩的风采,同时也为今天的版画家回归本土艺术,建构有中国艺术特色的版画体系指出了回溯的源头和支点。
其二,《通鉴》对每一幅作品除了名称、年代、尺寸、地域和刻印商号外,还撰有关于该种类的评点文字,以显示该种类的起源、演变及相互影响关系,这是本书不同于其他相关研究的另一特点——细致。比如清代苏州木版画《陶朱致富图》是以“泰西笔法”刻印的带有西洋写实风格的作品。作者在中堂画名目下的名胜繁花条目中,先借画上题诗,点出这是切中一般世俗的心理。然后引出“陶朱致富”典故出自范蠡,再分析作品丰富的内涵,评介艺术手段的精湛。如此精当而独到的论述,读之可对作品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分析方式贯穿全书木版画的每一类每一种,展现出作者对木版画独特的认识、把握和评判,也为后来者研究木版画指出了向上的研究途径。
三 “在一般中看出优异,在大众中托出精英”
张先生关于中国木版画的认识与研究不只是在分类编纂上的独到,更体现在对于各类木版画的寻根溯源和精彩归纳中。中国学术传统有“知人论世”之说,假而用之则为木版画与字画刻印之关系的探究。张先生在上卷“历史长河——一千二百年”中,尤重这样的寻根溯源的论述。《通鉴》一开篇就上溯到中国木版画的真正源头,从结绳记事到河图洛书,从竹简木牍、印章碑拓的刻写到纸的发明、木雕刷印的工艺技术,对于木版画的渊源、演变及其特点一一考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考索,张先生说:“尽管有很多都湮没了,仍然有不少麟角凤觜,值得我们珍视。不论是考古的发现还是传世的作品,就象是里程碑一样,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还会了解到当时的一些其它信息。譬如说它怎样被宗教所利用,成为佛教的宣传品;怎样成为书籍的插图,以致发展到有文必有图的程度;而年画的出现使其贴近了群众,使节日的色彩更加浓重。”(《通鉴》,49页)这种对于木版画在历史发展中用途上的拓展、流变的研究手法,探寻一个画种、一个门类、一个母题的来龙去脉的方式,在20世纪的木版画研究中,甚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恰恰是这种瞻前顾后的治学方式才能真正地让我们触摸到中国艺术迥异于西方艺术的历史殊相和独特之处。
寻根溯源的方式也是为了更好地显现传统艺术的精华之所在。在下卷论述如此庞杂繁多的1200多幅木版画时,张先生总结其方法:“将年画和文人的笺谱并列,民间的纸马与名人的画像并列,食品的包装纸与国家的纸钞并列,好像有失体面,‘下里巴人’怎么能与‘阳春白雪’并举呢?这正是著者的用意。要在一般中看出优异,在大众中托出精英,在俗中显出雅,在两千多‘下里巴人’中唱出二三十‘阳春白雪’来,这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整体。”(《通鉴》,604页)从这段精见迭出的文字中,我们也看到了张先生研究木版画的用意和目的,“在一般中看出优异,在大众中托出精英”,这不但对于中国木版画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艺术史也能有所禆益。精英与大众,优异与一般,雅与俗,看似有上下、高低之分,实则是一个互动关系,精英从大众中来,优异自一般中出。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类都无法凸显木版画传统的艺术精髓,也无法目及整个中国木版画的全景,也就无法把握民族艺术发展的脉络。
《中国木版画通鉴》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研究著作,弥补了中国木版画整体研究的不足。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中国木版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产生示范意义,中国艺术的自信与复兴也可期日而待了。